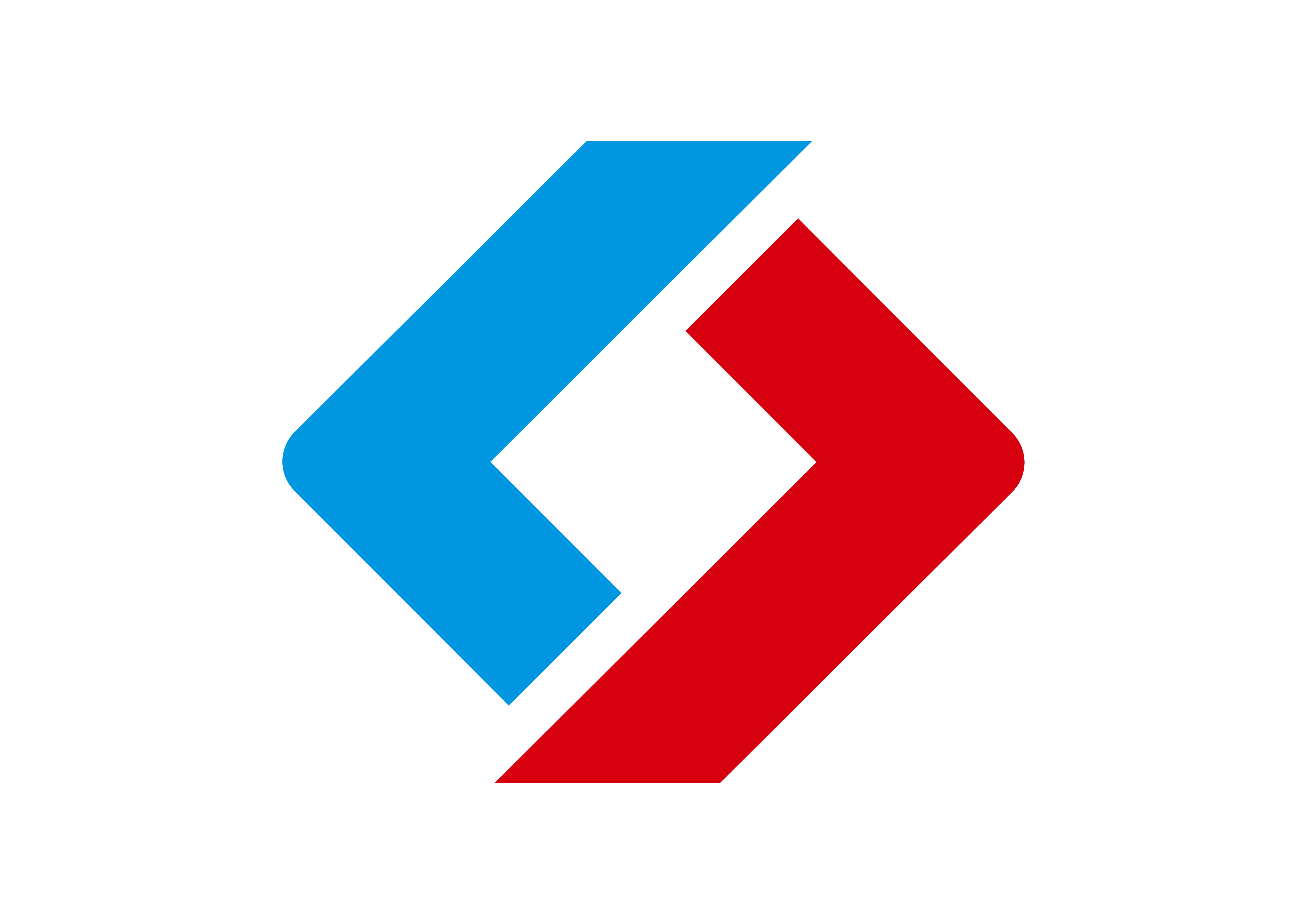沈从文写作教学指导
发布者:cj_zqw 发布时间:2016-05-13 08:30:39 点击数: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大师云集。“它的文学院不仅出大学者,还出大作家。”①当时联大的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沈从文、陈梦家、李广田等,外国文学系教授钱钟书、冯至、卞之琳、柳无忌、吴宓、陈铨等,他们各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等著述,都是文学修养一流的人才。汪曾祺、林蒲、吴纳荪、郑敏、袁可嘉、杜运燮、穆旦等都是联大文学院毕业后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晚辈。“汪曾祺说他报考西南联大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沈从文也很欣赏他,最终汪曾祺成了沈从文的高足。”②直到晚年,汪曾祺还带着点孩子气地宣布,自己是沈从文的“得意高徒”。抛开师生相处形成的私人情感,沈从文先生到底教给汪曾祺什么,让他多年之后,在梦中仍像小学生般恭敬聆听老师的教诲?“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③文学创作和作文教学方法相通,我们仔细研读《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不仅能破解“创作能不能教”这个难题,而且能发现沈从文先生“得法”的写作教学秘诀,对当下的作文教学不无启迪。
一、先“写”后“讲”,评讲要有针对性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④常常见到,当下的一些作文教学就是老师先传授一下“写作秘诀”,然后布置作文,让学生自己去写,写完了,交上来教师批改,写个评语或打个分,训练就算结束。碰到好一点的作文,老师就做示范作文读一读。久而久之,喜欢写作文的寥寥无几。应该说,当下的作文教学对“讲”是十分怪异的:在作文指导阶段,大讲特讲;在作文评讲阶段,惜“讲”如金。“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⑤作文教学不能空谈高头讲章,而应实实在在地教学生写作:不仅要关注写前指导(命题、立意、选材、结构等),更要注重写后评讲(师生探讨、学生互评、二次写作等)。无数事实证明,仅仅注重写前的“讲”,忽略写后的“讲”,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低效的。
成功的作文教学总是要关注学生的习作。评改作文的要求要具体,操作性要强。“失”,要有行之有效的提高措施;“得”,要有起到积极引导作用的恰当评价。茅盾先生上小学时,老师在他的《宋大祖杯酒释兵论》的文末,写下这样的批语:“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少年的茅盾该是如何受其感发和激励!学生的写作水平是不均衡的,有的作文甚至只有个别句子、词语较为精彩,那么老师在写评语的时候,就要抓住学生的这些闪光点,来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文中的两个比喻句很美妙,独特,读后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很喜欢,希望以后还能享受到,老师相信你!”虽然寥寥数语,但这种激励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二、化整为零,从片段练习开始
“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⑥沈从文先生曾经以“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等题目来训练学生的描写能力,对较为出色的习作,再推荐发表。他认为,作文片段训练能把细致的观察思考和写作结合起来,从而逐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片段作文相对于整篇文章的写作,它突出某一种单项写作能力的培养,可以描写生活中的一个细节,说明事物的一个方面,谈论对某事某现象的一点看法……这种分解的写作练习往往是通往高层次创造性活动的基础,可以帮助初学者尽快累积起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最初的基石,这些基石是构建个性化作文创造之塔的有力积淀。精致的片段是完整篇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件,“聚沙成塔”“垒砖筑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始于垒土”,片段作文训练之于篇章作文就是聚沙、垒砖、垒土的过程。片段训练得法,就可以顺利过渡成篇;片段训练扎实,就不愁写不出鸿篇巨制。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有强烈的片段训练的意识,只要长期坚持训练,就能不断提高写作能力。
三、立真求诚,朴素也能创造诗意
“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⑦朴素的文风,是写作的一个基本底线,也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它要求写作要诚,要真,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写,落在纸上的文字一定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不能说假话、空话。沈从文的《萧萧》,在写这个乡下童养媳时,从来不照搬城里人的语言,不用“懵懂”“浑浑噩噩”来描述萧萧,只是说“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沈从文说他从来不让小说中的人物为自己代言,不去刻意地拔高他们。他同情自己笔下的人物,却不人为改变他们应得的运命,这样的写法方能写出一个个真实而“活”着的人。又如在《边城》中,祖父对翠翠说:“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方配活到这块土地上。”这句话既非豪言壮语,也无华丽辞藻,但它是饱经沧桑的老船夫的人生信条,确是一句内涵深刻的临终嘱托。沈从文创造了他的“边城”世界,汪曾祺也创造了自己的“高邮”水乡,从某个角度看,他们都在用朴实的语言“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那条河串起了无数的故事、风景和人生,他们都想做那河岸边的诗人。
《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引导学生表达真情实感,不说假话、空话、套话,避免为文造情。”作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就应该是引导学生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做真人。在教学中我们时常发现学生的周记或自选题作文往往较命题作文、考场作文写得真实感人,自然流畅。原因何在?因为在周记这样的写作活动中,学生没有处于压抑状态,没有说谎的必要,没有为炫文采而炫文采的需要,敢于袒露真实的自我,而在考试作文中学生为分数而写,在高分作文的“诱导”下,违心地“为文造情”“为文造采”。
四、亲自下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⑧“他称他的小说为‘习作’,并不完全是谦虚。有些小说是为了教创作课给学生示范而写的。”⑨沈从文先生不仅帮助学生修改作品,引导学生进行专题性的阅读,而且亲自写作示范,树立标杆。长期以来,我们语文教师对作文教学指导方面可谓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有多少语文老师在坚持写下水作文?有多少语文老师有写作的习惯?语文教师自己不动笔写作,不能做示范,如何能指导学生写作?这岂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我们老师能像沈从文先生那样,来一点亲身示范,那效果会怎样呢?教师只有亲身实践才能知道写作的甘苦,才能更好地把握写作规律。教师能写出作品才有说服力,不能下水作文,就如站在岸边教人游泳,虽然口若悬河,但效果如何,不难想象。
上世纪六十年代,叶圣陶在《文汇报》发表了《教师下水》一文,他旗帜鲜明地倡导“教师下水”练笔。其目的“无非希望老师深知作文的甘苦,无论取材布局,遣词造句,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非常熟练,具有敏感,几乎不假思索,而自然能左右逢源,这样的时候,随时给学生引导一下,指点几句,全是最有益的启发,最切用的经验。学生只要心领神会,努力实践作一回文就有一回进步”⑩。语文教师必须下水写作,已成为语文界的共识。没有“下水”的体验,老师对写作的指导往往隔靴搔痒;有了“下水”的体验,教师的指导更容易对症下药。
五、身教胜言教,功夫在课外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沈从文先生从一个小学毕业生,通过艰苦不懈地努力,成为“星斗其文”的一代文学名家,是值得后辈学习的励志丰碑。在平时的教学中,沈从文先生朴实、真诚地热爱着学生,体现了“赤子其人”的高尚品德。
语文教师的修养是多方面的,如文学修养、口头表达修养、课堂教学艺术修养等等,但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阅读写作习惯更为重要。作文问题也是做人的问题,教师在做人方面的一言一行会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做人的质量决定了作文的质量。语文学科是一门人文性浓郁的课程,人文精神不能靠强硬的灌输,它重在熏陶,重在润物细无声地感染。在这过程中,教师示范引领的榜样作用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的。教师是一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了,才能更好地完成语文教育的文化使命。一个品德高尚、积极进取的语文教师往往具有较为全面的素养,有了这样的“内功”,方能可亲可敬,春风化雨,“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沈从文先生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写作能力应该是源自每一个自我言说、倾诉、想象的内心需要,只要施法得当、动之以情,是能进行有效训练与培育的。
注释:
①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第32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8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③④⑤⑥⑦⑧⑨?曹鹏选编,《汪曾祺经典散文选》第83页,第83页,第83页,第84页,第84—85页,第85页,第23页,第8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
⑩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下册)第488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