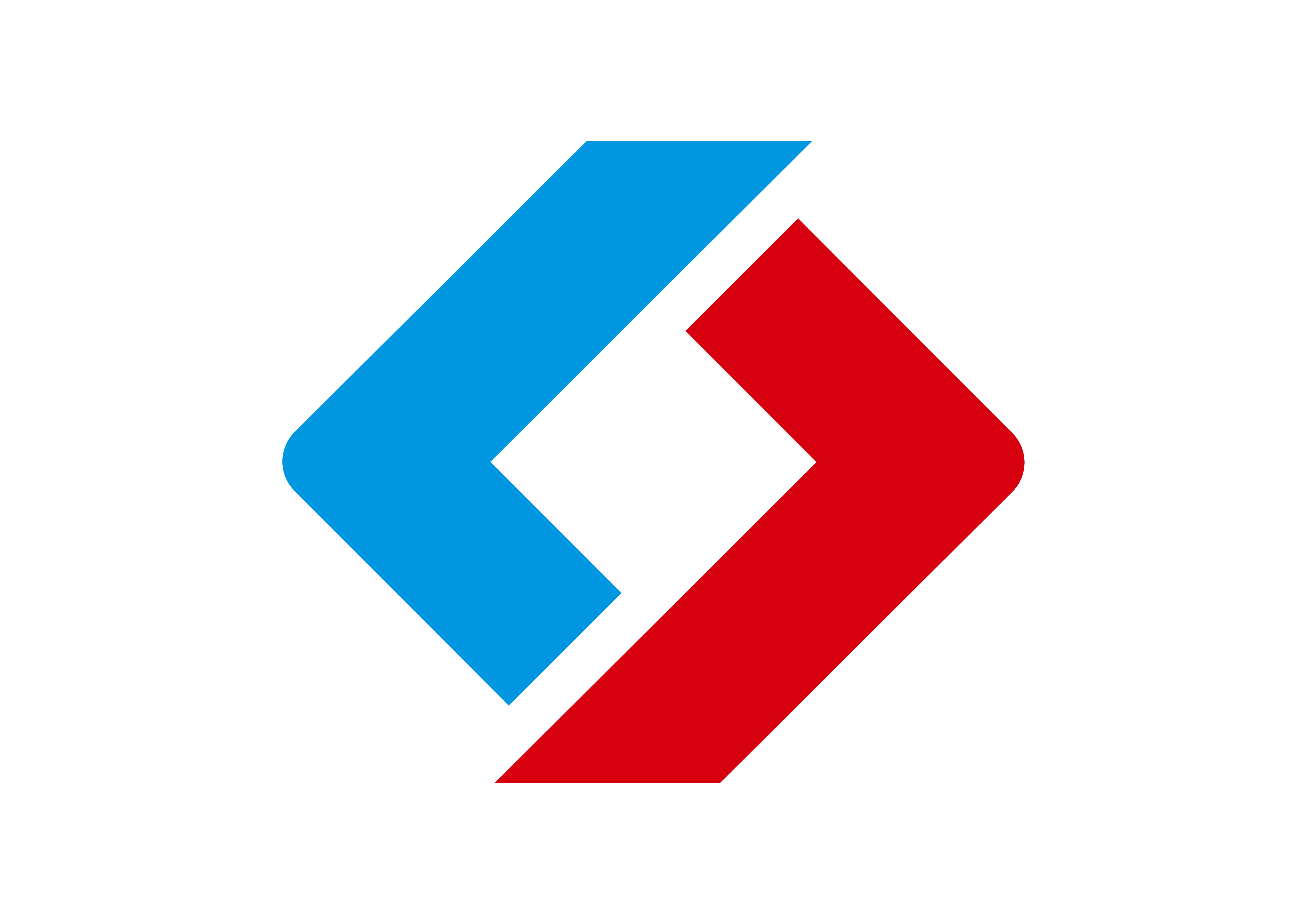王蒙:我一看民国剧就“晕”
发布者:cj_ysh 发布时间:2015-05-04 09:23:50 点击数:
民国时期的语汇与官衔
现今一些描写民国时期的电视剧,一听里边的对话我就几乎晕倒,因为只要说上三句话就露馅了。
提起中华民国,对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伪的“中华民国”,原因是日伪政府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执政党”仍然名为国民党。不同之处是“国旗”上加一个小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和平”,意味着汉奸路线,不准抗日;“反共”,以此标榜,耐人寻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条口号就是“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当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学校紧紧张张地要求我们背诵,说背不下来就有可能被“带走”,可以看出日伪势力是如何地视中共为心腹大患,为头号敌人。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敌伪口号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做了铁证。
还有令人困惑的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原汪记的汉奸国民党党部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告同胞书》,大张旗鼓、大言不惭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并高喊“蒋总裁万岁”。原来说的是“汪主席”“陈(公博)主席”如何如何,眼也不眨,立马换成了“蒋总裁”,让少年的我大惑不解。此后,未见到处理汪记国民党机构的任何后续消息。
后来报上出现了关于国府“接收大员”的报道。国民党贪官污吏当了大员以后颐指气使,化公为私,什么“五子(房子、车子、票子、儿子、金条子)登科”啦,什么发国难财、接收财、娶接收夫人抗战夫人(把沦陷区的夫人抛弃娶新夫人)啦,不一而足,这些事情,在报纸上爆料,使人深感失望。
大员,这是民国时期对于官员的一种说法。那时说到高一点儿的官员,还有要员、要人一类名词,对他们绝对不叫领导也不叫首长,而叫上峰、长官、×座(如局长就叫局座,主任就叫主座),夸奖一个官员时说他“忠党爱国”,说部级副职时不叫副部长,叫次长,说到“汇报”,绝对只能叫“报告”。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叫党部,绝对不叫什么省、市、县委员会。而那些不学无术的国民党政工干部,被舆论称为“党棍子”,国民党召开的动员会长官讲话会被称为“精神训话”,某些会议开始时的默哀,日伪时期称作“默祷”,国府时期称作“静默”。这些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很多词儿如领导、任务、组织、首长、汇报、总结、经验、教训、坦白、从严、从宽、贯彻、摸情况……都是解放区的词儿,国府控制区绝少用这样的词儿。现今一些描写民国时期的电视剧,一听里边的对话我就几乎晕倒,因为只要说上三句话就露馅了,剧中我党的谍报人员等于不打自招,国民党方面的人员也似乎是刚刚受过解放区的“洗脑”的“新生”人员,国共双方谍报人员满嘴都是老解放区的名词。
此外,其时将公务人员与教育界供职者称为“公教人员”,大体上是指工薪阶层的白领。民国时期称呼男人为先生、×公、公子、少爷、老爷、老板,称呼女人为小姐、太太、老板娘。小学时称老师为“老师”,中学以后称“先生”(不分男女),称班主任为“级任老师”。称呼商家为“掌柜的”,称呼服务员为“侍应生”“跑堂的”,称呼管家、幕府人员、秘书等为“师爷”,称呼会计、出纳为“账房先生”,说到妓女称为“窑姐”,说到小偷扒手称为“小捋”,公安局叫警察局,派出所叫“段”上,女仆叫“老妈子”,男仆叫“听差”,家务劳动介绍机构叫“妈妈店”,机关学校的勤杂人员叫“管役”,这些用词与解放区、新中国的称谓完全不一样,差远了去啦。

年仅14岁的王蒙在河北高中就读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图右为中学时期的王蒙。
民国报刊
那时的报纸还有一个说法,将大学生中致力于反蒋的学生称为“职业学生”,即他们不是学生,而是以学生的身份打掩护,专搞颠覆国民党政权的。
当时北京有三家报纸我印象深刻:一是国民党党报《华北日报》,销路很差;二是民营报纸《平明日报》,销路不错,副刊上看到过萧乾、焦菊隐的文章;三是日伪时留下的《实报》,小开张,人称“小实报”,八卦新闻多,主编管翼贤,解放后1950年代以汉奸罪被处决。“小实报”的版面至少有三次给我留下了印象,一个是日本发动突袭珍珠港后,宣布开始了“大东亚战争”,《实报》上登载有什么人摇旗助威庆贺(后随着战况失利日方更名此战为“保卫东亚战争”)。二是详细报道了枪决汉奸、间谍金壁辉即川岛芳子的情况,说什么金被处决前要求换上一身素白衣裳,被国府执法人员拒绝。三是报道冬季慈善粥厂开张的消息。我那时还能见到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1946年旧政协会议达成停战协议(没能执行),《大公报》用头版通栏刊登四个特号大黑字“停战令下”,非常醒目。
说起民国的期刊,日伪时期不能不提到《三六九画报》,即每月阳历三日、六日、九日,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出版的娱乐小刊,封面多是名伶,即京剧坤角,如言慧珠等的黑白照片。该刊版面上我有兴趣的内容有郑证因的《鹰爪王》,叫作“技击小说”,没有叫武侠小说,还有白羽的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此画报社举办过短篇小说大赛征文,获冠军的小说题名《点绛唇》,是凄婉的爱情故事。
国府时期,有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主张第三条路线,我的印象是它的文字语言比较古雅与学院气,少年的我读起来比较吃力。另外在旧中国临近寿终正寝了,忽然出了一本《太平洋月刊》,主编姓耿,笔名“笑天”,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叫《列宁的叛徒与国父的逆子》,破口大骂完了国民党再骂共产党,十分吸引眼球,一下子洛阳纸贵,但没出几期,严正宣布停办,未知其详。
1948年,一家赔本的小报突然别出心裁,发行了套红号外,声称“共军”的刘伯承等已被“国军”俘获。为此,国府有关部门宣布此报造谣传播失实消息,欺骗读者,罚他们停刊一周(或更多)。其实,他们正是因为报纸办不下去了才玩这么一手“奇葩”,光这样一份号外,已经赚回了不少亏空,你不停它的业,它也早想洗手不干了。
我那时爱看报,许多消息是从报上得来的。1948年年初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当选为大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江南一家报纸说蒋中正当选为“小总统”,后来说是经查确系排版紧张所致,没有政治意图。“受害人”蒋介石也未提出诉讼,不立案。还有一事,中国国民党一个机关的牌子被示威学生换成了“中国刮民党”,于是一批人在报纸上表态,说是该党受到了严重污辱,令人哭笑不得。国民党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后报上登了许多对嫌犯的审讯消息,居然还大量刊登了他们对闻、李的咒骂,连“嫌犯”的捶胸顿足、情绪激动、流泪喊叫都有报道,似乎是在宣扬“杀之有理”。1946年美军皮尔逊强奸北大学生沈崇案发生后,各报纷纷连篇累牍地刊登对沈崇的妇科检查病历,污七八糟,观感十分恶劣。1947年四川说发现一个女子杨妹不需要吃饭,国府组织了国家级专家去调查,后来报上登的调查结果是在她肛门上发现有食物残渣,说明她不是不吃饭。为此引起媒体冷嘲热讽,说国民政府主导的我国科学专家的最大科研成果竟是人类必须吃饭才能生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关于郝鹏举的报道令人难忘。郝鹏举是个有名的变色龙,他在国共日伪之间来回反水。1946年年初,民国方面的媒体报道郝鹏举的日伪军部队要从“共军”处投靠蒋军了,可是没几天说是没有此事,并说是郝受到共军高级将领的看望宴请云云,个把月后又大张旗鼓地报道,说是郝司令当真投蒋了,数周后,却是郝司令被共军枪决了。
民国时期的报纸有一套专门语言,战事失利撤退,叫“转移阵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打死,叫“自行失足”,其实“自行失足落水”的说法早就受到过鲁迅的声讨。那时的报纸还有一个说法,将大学生中致力于反蒋的学生称为“职业学生”,即他们不是学生,而是以学生的身份打掩护,专搞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根据我个人对旧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了解,“职业学生”实属罕见,相反,地下党的要求是进步学生首先必须学好功课,才能在同学当中树立威信。倒是有几个“职业教师”,例如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校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杨伯箴同志,解放前在北平的身份是某校童子军教员。杨后来担任过北京师范学院院长、外交学院院长等职。
百姓生活
当时的我们恨不得引爆旧世界,把旧北平彻底翻一个个儿。
那时失业人口极多,我们家住的西四小绒线胡同一带大多数人都没正经工作。有房的人家出租一两间,勉强维持生活。再有就是过往略有积蓄的人,靠卖上一辈的遗物维持生活。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些邻居祈祷上苍,希望给自己以机会捡到一个装满大票子的皮夹。

民国时期的街头乞丐。
那年月到处是垃圾堆,我在西四、西单、东单、北沟沿都见过大垃圾堆,苍蝇嗡嗡叫,恶臭扑鼻,小孩子在上面捡煤核,有时捡到残羹剩饭,就吃了。报上经常出现“由于误食垃圾鱼头一家人惨死”一类的消息。1946年年初我11岁,参加了国府第11战区政治部举行的中学生演讲比赛,我当时就说:“看看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哪里去了?”我的演讲稿得到了当时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的叶剑英同志身边工作人员李新同志的指导。由于我的讲话的调门不符合主办者的要求,虽然我的演讲反响最热烈,连一个主持发奖仪式的军官都说“王蒙那个小孩讲话声如洪钟”,可是仍然只给了我第三名。
北平一解放,没过几天,解放军就用车拉走了所有市内的垃圾堆,真是说干就干,立竿见影,赢得了民心。
当时北京的大街是柏油路面,胡同里都是土路,俗话说“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我解放后在钟敬文教授家中看到过一幅字,上面有一句说的是在北京的生活感受:“日日好春风里过,教人梅雨忆家乡”,意为北京的风水劣过江南的梅雨。那时北京下水道问题严重,大雨后有些地方水可没膝。雨后到处是蜻蜓,入夜则是萤火虫到处飞舞。那时候萤火虫多除了生存条件与此后不同以外,主要是由于电力少,常常停电,供电时贫民也舍不得开灯,给了萤火虫光芒四射的机会。小汽车很少,公共交通靠有轨电车,车上挤得连门窗上都扒着人。这种场面我1999年去印度访问时又看到了。我们那时青少年普遍不买票,想买票也买不成。
民国街头,刺激人的还有乞丐的群相。我们居住的胡同里常有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女丐带着一个小女儿行乞,她的表现被认为是疯癫,有时小学生下学时看到她们,一些淘气的孩子就七嘴八舌地叫:“疯子,疯子!”这时女丐会惨叫一声吓得所有的路人疯跑。我不懂为什么那时候的孩子完全不懂得同情贫民与弱者。
有一种叫作“叫街”的乞丐,他们走的是骇人听闻的自我施暴苦肉强讨路线,见了他们估计有钱可给的乞讨对象,就用砖头砸破自己的脑袋,砸青自己的胸口,甚至用利刃划开自己的脸面,血流满面地跪下乞讨。令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种乞丐,寒冬腊月,破衣烂衫,天色已晚,他睡到你家门口,吓得居民赶紧掏钱送食物,只求可怜人不要死在自家门前。
再有就是各种生理畸形或残疾的乞讨者,惨不忍睹。
这样的乞丐群相,我的感觉是历史通过他们在进行发动人民大革命的动员课,倾情发力,号召颠覆造反。一个国家,能够这样混下去吗?这里不发生,这时不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难道能发生什么温柔美丽的沙龙派对吗?
现在重温那时的北平旧照片,萧疏、陈旧、破烂、贫穷、饥饿,摇摇欲坠,是彻骨的绝望感。当然也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例如城墙、牌坊、灰瓦顶子、平房、四合院,还有那时不拥挤,全北平只有200万人,而现在是2000多万人,等等。再说怀旧就是怀自己的少年时代啊,谁能毫无这种向后看的波动呢?但当时的我们恨不得引爆旧世界,把旧北平彻底翻一个个儿,《国际歌》的词儿叫“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终于等到到处是高楼大厦了,又会怀恋旧日的某些特色或遗憾于某些旧日图景的失落。文化就是这样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时时在失去,时时在创造积累。当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愤然!
学校经历
我的地下党单线领导人对于我与另一位进步学友双双考入河北高中,深为满意。
1945年我跳班上平民中学(今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初中,校长常蕴璞(字玉森)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工作非常负责,督导大家背“总理遗嘱”,多次在大会上讲“管学生必须体罚,一定要造成不守纪律孩子的肉体痛苦”。有时上课,我忽然听到后边啪啪打耳光的声音,异常恐怖,我们都不敢回头看,那是校长从后门悄悄进来,大打出手,打那些他认为不守纪律的学生。
南沟沿有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机构,一天级任老师通知我们班几个功课好的同学去那里座谈。我年龄小,一声没吭,听见几个大个儿学生提意见,说三青团员净是歪戴着帽子的纨绔子弟,和小流氓一样,给人印象不好。
我随后唾弃了三青团,去追求革命追求左翼思潮。我在国会街北大四院欣赏了大学生们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只觉得是惊天动地、气贯长虹,左翼意识形态尤其是文艺的气势压得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1946年,我所在的平民中学通知全体同学收听市社会局局长温崇信的讲话。他是公鸭嗓,南腔北调,全部腐朽透顶的国民党套话,没说一句明白话,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根本不会说“人话”,连我父亲在家听了此人讲话也完全目瞪口呆,莫名其妙。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政权要完蛋,首先表现在语言上的撑不起门面来,简单地说,就是说不成一句人话。
当时的平民中学给我印象深的是音乐教员乔书子(音),他一面教着我们课一面晚间演出着歌剧,人的样子也极帅气。他自己也作曲作词,如“第一次的春雨,只是几滴,像少女第一次的眼泪,我问你,什么是你第一次的悲哀呢?”据说,他也可以教授“国文”。平民中学的校歌词曲也是他作的,唱的是“你是智慧的海,你是真理的灯”,追求高远。
教学楼前有几株大合欢树,一到放暑假的时候,红花盛开,着实难忘。
高中时我上了河北高中(简称“冀高”)。这个学校有革命的传统,“一二·九”运动中,河北高中的许多学生参加了以大学生为主的游行。荣高棠、康世恩等都曾在这个学校就读。19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学生自治会成立,校内的中统特务和国民党警察局配合,大打出手,一次就逮捕30多个学生自治会人员,使学校进步力量受到打击。为此,我的地下党单线领导人对于我与另一位进步学友双双考入河北高中,补充进去,深为满意。我们的考入,使冀高增加了一个地下党的平行支部。冀高原校址现在是地安门中学,该校至今以每年4月17日为校庆。
我在冀高时,用复写方法办了一个刊物《小周刊》,手抄的,抨击社会不公,被校长穆庚寅找去谈话,说是办这种周刊会造成事件,下令取缔。但冀高仍有大量党员与盟员(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在活动,有两个平行的党支部,以便于与国府周旋。学校也有中统组织,他们以“暮鼓社”名义张贴大字报和“肃清匪谍”一类标语,但谁也不知是谁干的,鬼鬼祟祟。
1948年寒假,河北省教育厅在冀高办冬令营,伙食糟糕,白水煮萝卜,没油,苦的;房间里温度在零下,有炉子没煤,冷到极点。年龄大的学生到教室偷桌椅,劈了当柴烧。当时我家也是这样,冬天洗脚水、尿都会结冰。
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野和华北野战军包围,国府方面在学校招募“自救先锋队”成员,意图垂死挣扎,与解放军拼命。后来这些人不战而溃,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惩处。
同时以傅作义为首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了包括军警宪三方面人士的执法队,打着执法队的旗子,开着卡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声称遇到“通匪”的“匪谍”,他们有权“就地正法”。
选编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四期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