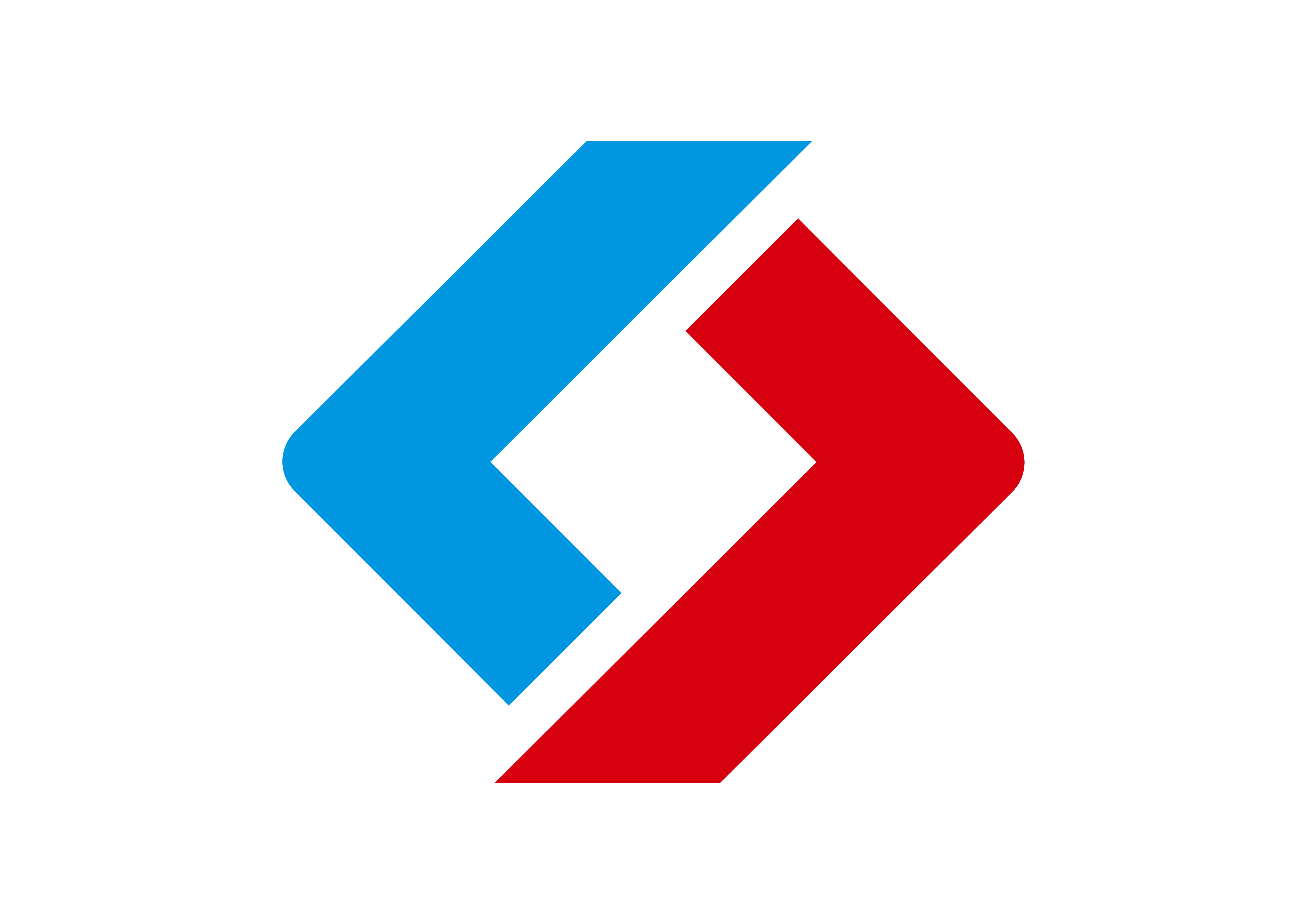“活教育”的理论基础
发布者:cj_lixia 发布时间:2010-07-09 10:08:05 点击数:
“活教育”的理论基础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并实验“活教育”理论,这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活教育”思想的形成,既是陈鹤琴长期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又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中、西文化与教育思想融合的产物。
一、“活教育”思想是在反对封建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
陈鹤琴认为,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比如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建起“西方式”的学校等等,但是中国的教育制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制约。他分析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传统的学校里的儿童,都是一些小可怜虫,他们机械地、被动地被灌输以有限的所谓知识食粮,而实际上他们却难以消化。不管他们认为多枯燥乏味,除了埋头读书外,别无他法,在教室四壁的梦坑、囚笼里,没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只要他们读和写,而从不要求他们自己去想去做。”陈鹤琴认为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少年儿童是不利于“民主和科学”的国家建立的,为了使这个古老的国家现代化,就必须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改革。而他的“活教育”理论正是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改革的一次伟大的尝试。陈鹤琴明确地指出,“活教育”是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而提出来的,他认为,“活教育”完全是一种新的试验。他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种子,生根发芽,开出花朵。”他又说:“所以我们对‘活教育’这一口号之提出,抱着无穷的期望,希望它能成为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符合民族精神的完善的教育制度,希望它能从理论走人实践,更希望它能由一隅一地之试验,发展而为普遍之推行。”可见,陈鹤琴先生把“活教育”理论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有力武器,对它寄予厚望,并且热情地投入到教育实验中去。
二、“活教育”目的论是在学习国外进化的文化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主要有三大部分:目的论、课程论和方法论。其目的论不仅带有鲜明的反封建传统的色彩,而且处处体现出对国外进步的文化教育经验的吸收和学习。
陈鹤琴说:“‘活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现代中国人。”即“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具体来说,“活教育”是培养具有以下几方面条件的“现代中国人”:
一是要有健全的身体。陈鹤琴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必须要有强健的身体,才能担当社会和国家的重任。他说:“在外国素来把身体的健康看得很重,像美国更把健康列为学校七大目标训练的第一项,这是何等看重身体的健全。”他要求国人向外国人学习,提高身体素质,摘掉“病夫”的帽子,以承担现代中国艰巨的事业。
二是要有建设的能力。他认为,现代中国急需一批努力于建设事业的人,应当从对学校的学生培养开始。他说:“就学校来说,学生在学校里应当训练他们从事于种种建设工作,大一点的为开辟校园、农场,设立工厂、图书馆;小一点的,修筑道路,整理桌椅,粉刷墙壁,布置环境,学校里面一切东西一有损破,就要学生自己去修好,一有缺点,就要学生自己去补救。过去学生建设能力往往太薄弱,现在我们要把它培养起来,以适应国家的需要。”
三是要有创造能力。他认为国民的创造能力对国家的发达是很重要的,他说:“时至今日,我们急需培养儿童这种创造的能力。”他列举了苏联、英国等国家重视儿童创造力培养的一些实例,要求在我国的教育中对儿童的创造能力加以适当的训练。
四是要有合作的精神。
他分析说,外国人非常注重团体工作,他们的合作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他说:“对于小朋友从小就要训练他们能合作,能团结,这才能使他们配做一个新中国的主人翁。”
五是要有服务的精神。他认为我们培养的儿童应该知道为人民大众服务,应以国家的前途、民族的生存为己任。
从陈鹤琴所论述的“现代中国人”的五个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主张从国外吸取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为现代中国教育所用,他努力在探索一条发展中国新教育的路子,而新教育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教育目的的确定。他概括出来的这五条标准,一方面反映了社会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他的教育理想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点。
三、“活教育”课程论和方法论是在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继承与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
陈鹤琴1914年―1919年在美国留学,1917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在此期间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他回国以后积极地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但是陈鹤琴先生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杜威的理论,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有选择地吸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之进行改造,形成自己具有特色和丰富内涵的“活教育”理论。陈鹤琴对杜威教育理论的继承与改造主要是在“活教育”的课程论和方法论中体现得比较突出。
1.“活教育”的课程论
陈鹤琴说:“‘活教育’的课程是把大自然、大社会做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他明确指出大自然、大社会是知识的主要源泉。他说,“从书本上能吸收的知识是死的,是间接的;而从大自然与大社会获得的知识是活的和直接的。不言而喻,在各个方面,后者大大优于前者。”
陈鹤琴对于当时学校教育中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现象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教科书也往往不能对那些不幸被迫去阅读它的学生们有所裨益,虽然书本内可能有丰富的材料,但它们是第二手的、片断的或者是表面的,甚至是虚构的。例如,对一个儿童授以有关蜜蜂的课文,可以教他蜜蜂如何嗡嗡叫,它的外形,如何酿蜜,但是儿童实际上从没有看到过书本上所讲的蜜蜂的实物。因此他对蜜蜂的印象,只不过是一种能飞、能叫、能酿蜜的小昆虫而已。这种死的知识有什么用处呢?”
从陈鹤琴这一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子。杜威的课程论中明确地提出以儿童的活动,即以儿童的直接经验为课程的中心,学校要围绕儿童的需要和儿童的兴趣来安排课程。他反对以既有知识编写系统教材,而且也反对用这种教材进行课程教学。他认为,让学生学习各种各样的学科课程,虽然可以学到系统知识,但是这样做的最大缺陷是把儿童同实际生活割裂开来,这样必然会阻碍儿童的生长。他认为,让儿童学习系统教材,无异于是学习前人的符号积累,从而远离了儿童个人的生活经验,使儿童学不到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杜威的基本倾向是反对传统教育中的分科教学,反对现成的、孤立于儿童经验之外提供的知识。他要求把课程和教材建立在儿童现在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儿童本身的活动就是课程,也是教材。他甚至提出要使儿童的学习“循着历史上人类的进步足迹前进”,“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重演一番”。在他所创办的芝加哥实验学校里,可以看到杜威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教材在各个方面进行的具体实验。实验学校的全部课程是由各种不同形式的主动作业表现出来的。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杜威对实验学校儿童的各种作业活动作了极其生动具体的描述,例如让儿童过原始人的游牧生活,像原始人一样借助简单的工具建造草屋、打猎、捕鱼等等。杜威说:“我要指出的一点,就是这样可给儿童很多机会从事真正的学习,很多机会去探究,终于获得了知识。”他希望儿童从对原始人及其活动的兴趣,扩展到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他分析说:“我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完全证明一个信念:儿童在一年内从事这种工作(每周共五小时)中获得关于科学、地理和人类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他们从那些自称以知识为目的的教学中,仅仅从被指定学习的固定课本中获得的知识。”
杜威关于课程和教材的认识和实验,是对传统教育脱离社会实际妨碍儿童身心发展的反拨。他关于教材与课程改革的见解有其合理性的,符合客观要求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夸大了儿童直接经验的作用,并且试图以活动课程完全取代学科课程,否定传统教育所使用的教材,这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陈鹤琴先生正是认识到杜威理论中的不科学性,他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杜威的理论,而是正确地肯定了书本的作用。他说:“我们并不是说在学习过程中要摒弃一切书本。如果恰当地用作参考材料,书本是有用的,但不应像过去那样,把书本作为学校学习的唯一材料。”他还对“恰当地用”作了具体的阐述。他分析说,“依照活教育的理想,国语、算术的课本教学也应当打破。不过依照目前中国的情形及社会上的传统习惯,一时尚不能取消。为补救起见,只有想法尽可能改善这些课本的内容及教法。”他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如何进行改革,例如,学校讲到鱼的知识,就要让儿童去看真正的鱼,让他们观察鱼是怎样呼吸的,是怎样浮沉的,并且还要让孩子们来解剖鱼的身体,研究鱼的各个部位,这样才会对鱼有真正的了解。陈鹤琴最后强调说:“儿童能够直接去学习,去研究,结果收获当然要比只靠书本的大得多。”
2.“活教育”的方法论
陈鹤琴说,“活教育的教学方法也有一个基本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他强调教学中应注重儿童直接经验的掌握,教师应积极地鼓励儿童去实践,去获得直接经验。他说,活教育的教学应“着重于室外的活动,着重于生活的体验,以实物作研究对象,以书籍作辅佐参考。换一句话说,就是注重直接的经验。”他说,“这种直接的经验就是使人进步的最大动力。”他认为儿童形成直接经验的过程,就是他们思维能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他们“自动研究”的精神形成的过程。他说:“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启发他们这种自动研究的精神。”他举了一个小朋友自己制作炮竹的例子,来说明自动研究的精神对儿童来说是多么地宝贵。他所说的自动研究精神实际上就是他的活教育目的论中所提到的创造能力。他认为这是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所应具备的品质。
陈鹤琴活教育的这一基本原则是受到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的启发,但是绝非简单的承袭,而是有发展创新之处。陈鹤琴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这一原则,可说是脱胎于杜威博土当年在芝加哥所主张的“寓学于做”(Learning by doing),但比较杜氏的主张更进了一步,不但是要在“做”中学,还要在“做”中教,不但要在“做”中教与学,还要不断地在“做”中争取进步。他又进一步对此观点进行阐述,他说:“教师与学生共同来做,必要时给学生以指导。他们在做与教中取得的直接经验,则是求得进步的主要因素。”陈鹤琴主张在“做”中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比如,通过教师对儿童的积极鼓励来促使儿童进步,他对此也举了一些实例,其中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有个孩子很喜欢弹琴,但是平时没有人称赞他,有一天有个教师夸奖了他,说他弹得不错,于是他非常开心,后来就经常练习,终于在这方面有所造诣。陈鹤琴通过这个实例来说明教师恰当的鼓励会成为儿童学习的动力,从而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陈鹤琴分析说:“假如你看见一个小朋友演说得好,你称赞他几句,这个小朋友一定会格外努力。”他认为“鼓励”是教师的一个法宝,要经常使用这一方法。他实际上就是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但是这一主导作用要同儿童的“做”联系起来,不能脱离儿童的实际,妄加干涉,否则只会阻碍儿童的进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与杜威认识的差异:杜威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只是起一种从旁协助学生活动的参谋作用,而否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陈鹤琴对此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学生在“做中学”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也不能脱离开教师适时的指导。他认识到教师指导的重要性,他提出,学生的“做中学”必须要和教师的“做中教”结合,才能在“做”中求得进步。陈鹤琴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
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对中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很雄厚的,它与西方的文化教育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有所改造,也正因为如此,“活教育”思想才有这样强的生命力。
(注:全文转自唐淑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的《童儿拓荒――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P145~152。)